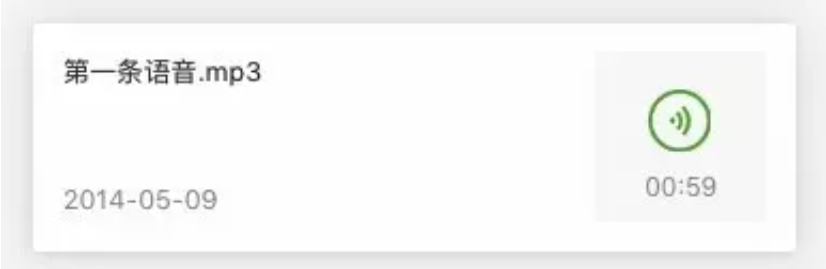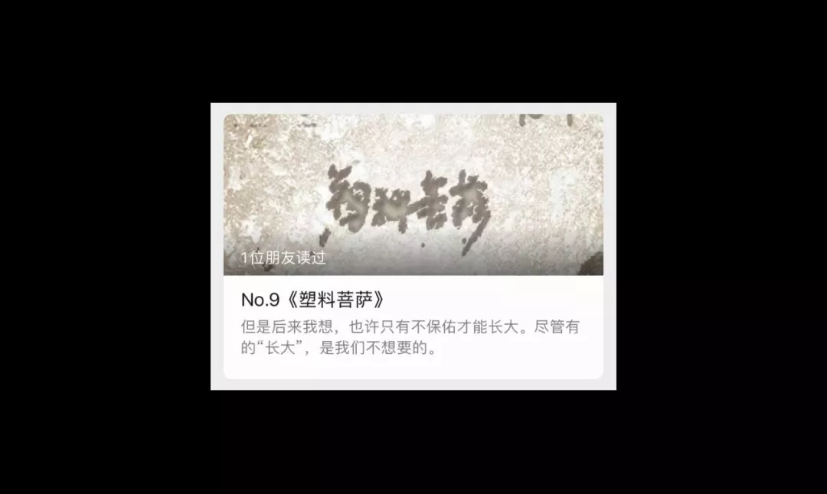艺人姜思达的另一张面孔,是内容创业者。在他为个人IP注入商业价值的同时,他的公众号「思达帕特」也经历了从自我表达到商业化运作的转型。在一番挣扎之后,他说,我仍然保留着创作心,无论是商业化还是非商业化的内容,我仍然坚持自己书写,仍然不胡说八道,仍然不生凑热点,仍然不标题党。
以下内容来自
我们也不必向内审视,这个过程非常辛苦,恐怕到最后也没有个像样的结论。我们很难肯定自己对于世界是全然拥抱的,更不确信自己始终被世界拥抱着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酷,是说我们不在乎,我们不在乎数据高低,但当一个高数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,酷的人突然不酷了,他会说一句很不酷的话,说:“我们总结一下,还能再怎样复制这样的效果”,或者“还能怎样取得更好的效果”。像是一个足够优秀的厨师,他的团队也会包装他的出身,说他曾看着父亲揉捏面团的双手。这些事通通没有对错,却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。当我回看自己的公众号思达帕特的时候,我不得不闲言碎语,聊聊这些。独立和受广泛认可,赚钱和守护内心,玩得开心和吸引外围,快速的目标和持续性的目标,这些都是我们想要的。每一件好事都有十足的魅力,我不够沉稳也不够决绝,我被这些价值持续羁绊着。所以我很难说,如今我写了一篇全然发自内心的文章,和本月有很多客户愿意在我的号做投放,哪个让我更开心。它们是不同种类的开心,也是我都喜欢的开心。一个是让我一天心情舒畅,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重要的,是突然间的自恋,和暂时性的内修;一个是让我这个月有了房租,可以发放团队工资,可以由此建立广泛的品牌关系。被自己认可了,和被别人认可了,我都想要。但是它们在我红了的那天开始持续打架,一直打到今天。2014年5月9号,也就是五年半前,我发了第一篇微信推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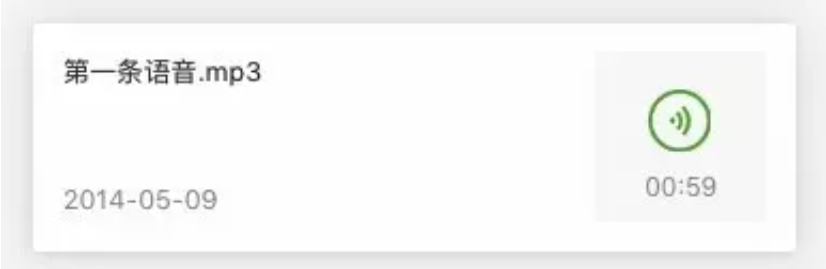
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审核失败。失败就是如此的没有道理。但这个失败势必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影响,也从某一个大二的下午开始,我抱着一台巨沉无比的电脑去咖啡厅开启自己的写作。那会儿每天我都能写3000字原创,其中还有大量的虚构,也就是短篇小说。我跟所有人一样,在回看自己曾经的作品时浑身不适,如坐针毡,觉得幼稚和造作。为了这篇演讲,我硬着头皮,回看了最早期的那些文章。看完之后,我半天坐在椅子上没动过。我定坐在那里,只有一个想法:我写得也太好了。

我是认认真真地觉得那时的自己写的很好,比如《厨娘》、《有一条被絮飞满的街》、《病》的第三篇《蝙蝠》、《普通杀人》,这些是虚构。
我记得写《厨娘》那天,那是一篇写了一下午的8千字短篇小说,讲一个贫穷女孩袁贤婷的故事。那会儿我已经能够赚些小钱了,已经懂得了如何穿着地更加时髦,出入高档餐厅的时候优雅点菜。但我还是会写“排班级座位的时候,她是唯一一个愿意和袁贤婷一桌的人。大家对袁贤婷的评价有三点:脑子有问题、穷、她妈太胖”——诸如此类,冰冷残破的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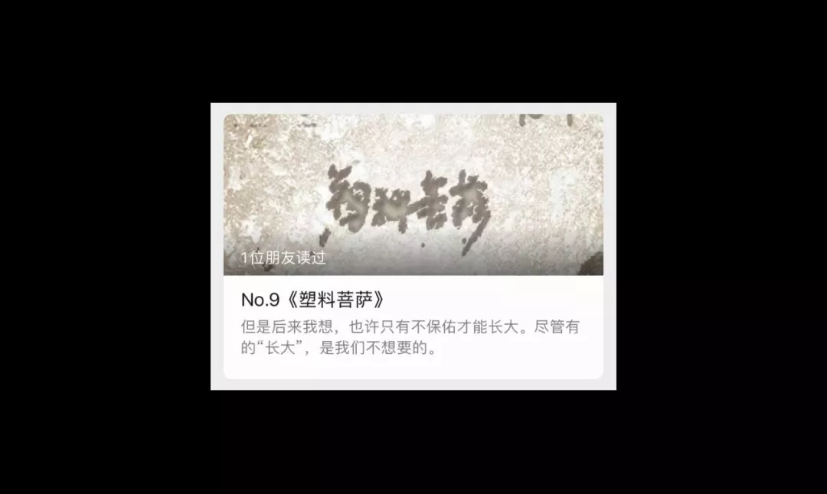
那会儿也写很多非虚构,比如第一个冲破宿舍范围内关注,在学校里收取了5000个阅读量的一个短篇,一千字左右,叫《塑料菩萨》,讲我小时候在公园玩套圈游戏,套中一个廉价的塑料菩萨项链,我把它挂在家,祈求我妈不要离开我去远方的故事。最后,我说“菩萨不灵”。我写完之后,在学校的咖啡厅里哭了半个小时。那个时候我会为自己的写作而共情,去感伤,去愤怒,去流泪。我像是一个情感极其充沛的生产机器,也觉得自己和那些严肃文学的作家没有太多质地差别。我承认我措辞的幼稚,或者结构不够轻快,但我一样可以在写作中拥有力量感,而不在乎是否给了别人力量。

写《在北京,他们飞驰》是写一群蹦蹦车司机,和新闻文体不一样,其实更像是一篇小品文。那会儿我关注到一个妇女,她给蹦蹦车装上了蓝色彩灯。即便她的车依旧是漏风的,也即便她的车随时会被城管扣留,但我依旧情愿幻想,她在装点这辆破车的时候,有一种轻快的欣慰,我甚至感谢她装点了我的夜色,让我在酒后靠在窗边之时,不见得更加狼狈。

我情愿非常自恋地感慨那时候写得好,是因为我从那会儿的文字里看到了自由。我无数次为品牌软文写作“要自由”“要这么自由”“要那么自由”,但我知道,自由不是口号,它是一种状态,一种感受,一种已经与我阔别许久的记忆。在我现在的工作里,为了一个远处的不存在的陌生人保持体恤,对一个无名的建筑物表达愤怒,是如此低效的行为,是一个做节目和开花店,一个拥有20多人团队的年轻创业者的残念罢了。
这位在大家面前的年轻创业者,拥有一定的商业价值,也对自己的商业价值进行了充分的开拓,他如今会每天开会,又要保持社交,他会接到很多广告,也有足够熟练的方法论,在半个小时内写出一稿过的推广文章。所以当他讲这些的时候,他是异常矫情的,跟使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一样矫情。这个矫情让他能够描述一点被普遍忽略的情感细节,又让他时常陷入一种道德焦虑。

思达帕特如今有四个核心成员,我,我的商务负责人,我的编辑和美术。在演讲之前,我其实已经向他们表达了我的道德焦虑:我挣扎在商业化和书写内心的边境上。他们回复我,在这份工作里他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创作乐趣,也在所有可能性下尽可能保留了自己的内心。我的美术说:“关于商业化,我没什么好讲,我觉得能赚钱,是好事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看到如此积极回应的时候,恢复平静和理智。但我终究不是一个理性驱动的人。
思达帕特集中展示了我的成长史,虽然到最后也只有我关心这份成长史。

我能看到自己视角的变化,能察觉到,如今为了一个提案否定若干的我,和那个会在半夜十一点突然发信息号召关注者在国贸站集合,相约在长安街走一整夜的我不一样。成长、变化、妥协、变机灵和变油腻,这些词汇只是立场差异罢了。归根到底,是思达帕特早已从我的个人仓库,变成了一个大敞四开的集市。阅读量高高低低都是表象,内在是,我很难说清我更在乎什么,和如果一定要二选一,我要选自己,还是选别人。“再小的个体,也有自己的品牌”。我何尝不是一个小个体,在把自己变成品牌的路上,我或许放大了自己的心脏,但又切断了自己的手指。我会为新完成的推送长舒一口气,又发现这口气,又长又飘忽。
有些事情会陪我走很远,有些只能走一段。我和每一个自己作别,向过去表达不舍,又在新的利好面前,笑脸盈盈。我曾非常残忍地思考,思达帕特到底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。现实情况是我仍要为此支付巨大的精力,而这对于创作其他内容体,比如节目、影像、甚至是花艺设计是一种抢夺。最后我并没有注销这个号,理由是看年终的利润,这个号的创收是非常优秀的。让它去留与否的标准,已经赤裸裸地变成了商业考量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非常残酷地长大了。我会为这一种长大,感到羞耻。即便这份羞耻在很多人眼里匪夷所思。我仍然保留着创作心,比如无论是商业还是非商业的内容,我仍然坚持自己书写,仍然尽全力去写让自己满意的文章,仍然不胡说八道,不生凑热点,不标题党。或许我和很多人相比,也算是有些坚持的人。哪怕都是开商店,都是要赚钱,我也更情愿让它是一个精品店,而不是大卖场。只是,我在翻看最早的自己,有一种惊讶:原来曾经的自己是那么单纯和执着,是自由和放肆。我为曾经的自己感到骄傲。想必我从那时走来,也不至于在这五年间就判若两人。只是我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,对自己的内心极度刻薄。我过于善于自我否定,最终把自己交付给一些粗暴的哲学:我写这篇演讲稿的时候泪流满面。那天的我不知道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会是怎样的神情。我想起了那个咖啡馆,和发布第一条语音时的盲目自信。我把那一刻的感觉抓了回来,在这里不负责任地自说自话。